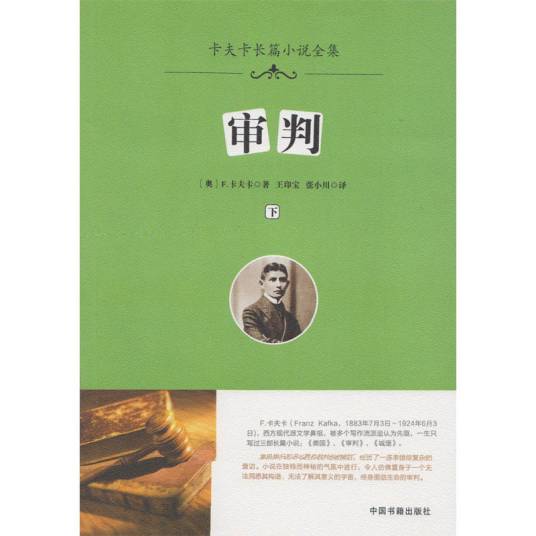-
审判 编辑
《审判》是奥地利作家弗兰兹·卡夫卡创作的长篇小说,1925年出版。小说叙述主人公约瑟夫·K在30岁生日那天突然被捕,他自知无罪,找律师申诉,极力加以证明,然而一切努力均属徒劳,没有任何人能证明他无罪,法院是藏污纳垢的肮脏地方,整个社会如同一张无形的法网笼罩着他,最后被杀死在采石场,这就是官僚制度下司法机构对他的“审判”。《审判》是卡夫卡三大长篇小说之一,其从出版之日起就受到各界的关注。
作品名称:审判
外文名:der Prozess
作品别名:诉讼
作者:【奥】弗兰兹·卡夫卡
文学体裁:长篇小说
首版时间:1925年
字数:152000
然而只要开始审判,就必然认定有罪,无法得到赦免。在这个法庭中,不存在无辜和有罪的区别,区别的只是已经找上你和暂时还没有找上你。K回想不出自己犯过什么过失,也不清楚有谁可能会控告他,于是他开始设法反抗法庭。他四处求人,甚至到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他力陈自己无罪,控诉在法庭的行动后面有一个庞大的机构在活动着,这个机构腐朽愚蠢,草菅人命。这个机构的存在只是为了诬告清白天事的人,对他们进行荒谬的审讯。
但一切都是徒劳的。最后,K连自己犯了什么罪都不明白,就在他31岁生日前夕的一个晚上,被两个刽子手带到采石场,“像一条狗一样被处死了。”
第一章 被捕——先同格鲁巴赫太太、后与比尔斯纳小姐的谈话 | 第六章 K的叔叔——莱妮 |
第二章 初审 | 第七章 律师——工厂主——画家 |
第三章 在空荡荡的审讯室里——大学生——办公室 | 第八章 商人布洛克——解聘律师 |
第四章 比尔斯纳小姐的女朋友 | 第九章 在大教堂里 |
第五章 鞭笞手 | 第十章 结局 |
时代背景
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已经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性的摧残与毁灭以及整个社会的异化是不容忽视的,人与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工业文明一方面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福祉,但它同时也导致人逐渐异化。作为对这一社会状况的反映,《审判》的创作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
个人背景
1914年,卡夫卡和未婚妻费莉莎准备结婚,但同时他还和另一个女人格莱特保持暧昧关系。在他左右为难、犹疑不定之际,发生了一件影响卡夫卡一生的事情:审判。此事须从卡夫卡对这场婚姻的态度说起。
卡夫卡本人确实不想结婚,但他又认为自己有义务完成婚姻这项职责。于是,他的内心充满了矛盾。卡夫卡想结婚的愿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他内心的真意,也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很可能他结婚的愿望越强烈,他就越感到内疚,越怀有一种强烈的罪恶感,而他的罪恶感越强烈,他就越想表明自己的真意,在结婚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积极的态度。这种恶性循环使他面临两场审判:现实中的与虚构中的。
1914年7月11日,审判终于来临。卡夫卡前往柏林看望未婚妻费莉莎,到达柏林的第二天,在他投宿的旅馆,由费莉莎、格莱特、费莉莎的妹妹爱尔娜以及曾为卡夫卡给费莉莎传信的一名作家瓦尔斯组成了所谓的“审判法庭”,卡夫卡则成为这个“法庭”上的被告。费莉莎措辞尖锐刻薄,指控卡夫卡的反复无常和不忠诚。卡夫卡默默地接受了这场“审判”。最后,“法庭”作出宣判:解除卡夫卡和费莉莎之间的婚约。
在31岁前夕,卡夫卡摆脱了和费莉莎的婚约,此时,他本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创作,但却得了一种“法庭恐惧症”。同年12月5日,卡夫卡接到费莉莎妹妹的信,得知由于她父亲一个月前心脏病猝发去世,她家的境况变得十分窘迫。由此,卡夫卡认为是自己一手造成了费莉莎一家的悲剧,他的内心充满了沉重的罪恶感。1914年12月,在内心痛苦的挣扎中,卡夫卡创作完成了《审判》。
值得注意的是,卡夫卡先写完了《审判》的结局,之后才诞生了其他章节。此书每章的标题均为卡夫卡所作,但章节的编排次序则是其好友布劳德根据回忆做出的判断。据布劳德所说:“卡夫卡认为这部小说还没有写完。在最后一章之前,一定还该描写这个神秘的审判的各式各样阶段。可是,根据作者自己的看法,既然这个审判永远不可能提到最高法庭那里去,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小说也可说是无法完结的。”就是说,小说可以延长到无休无止的境地。
约瑟夫·K是一名银行襄理,在被宣布逮捕之后仍可以外出,上班,谈恋爱,只在审讯的日子才去法庭。可是,却并没有合乎法律程序的名副其实的审讯。法官甚至不了解被捕者的真实身份,而询问K是否是一名油漆匠。接下来,他遇到了一个又一个与法院熟识的人。住在法院的负责法院杂务的门房女人,K的叔叔给他找的律师先生,银行的客户一个大厂主给约瑟夫介绍的法院专职画家。就连K准备陪同意大利商人去参观的教堂的神父也是法院的监狱神父。小说中与法院的有关的人都声称自己能够帮助K,但却谁都没有真正将K从法网中解救出来。而K本人却越来越看清法院及司法制度的肮脏内幕。
布尔斯特纳小姐
布尔斯特纳小姐和K同是格鲁巴赫太太的房客,在被捕事件发生以后,K第一个想要求助的对象就是布尔斯特纳小姐。K等至深夜,并且因为格鲁巴赫太太对布尔斯特纳小姐的不满和格鲁巴赫太太发生不愉快。他是维护布尔斯特纳小姐的。直到K向她讲述被捕的事件时,布尔斯特纳小姐对法律的知识了解不多,近乎无知,她不是从事跟法律相关的工作的,而她要到下个星期才要去一个律师办公室工作。所以,K等待布尔斯特纳小姐想和她讲讲被捕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她能给他在这个案子中以实质性的帮助,而是他需要倾诉。
门房妻子
门房在法院的地位很低,他的妻子因为与法官有染,而存在帮助K的可能。门房妻子引诱K,并且主动提出帮助来诱惑K。虽然K不信任她,但是他依然找不到什么站得住的理由来拒绝这种诱惑,并且他想通过与这个女人建立关系来报复法院。但是这个女人又让K失望了,她虽然说很想让K带她逃离那个地方,但是当学生带她去见预审法官的时候,她自己的行为又表现出她自己不想离开。
莱妮
莱妮是K去拜访霍华德律师的时候认识的。从一进门K便对这个小看护产生了兴趣。他对莱妮有一种生理上的吸引,当他得知莱妮认识很多法院的人的时候,他又期待莱妮能够在这个案子中给他提供帮助。但是在莱妮的引诱下,K也是极为不理智的。他不顾莱妮是律师的情妇这样一个身份,不顾他的叔叔正在跟律师和法官周旋,把自己的案子抛之脑后,与莱妮发生关系,这使得K失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最后,K不顾莱妮的劝告,坚持解聘律师,从而使他陷入困境。
作品思想
权利主题
索克尔认为:“《审判》是卡夫卡主要作品中唯一真正难懂的,原因有二:法庭全然的模棱两可和主人公全然的矛盾心理。”正因如此,这部作品自面世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争议。争议主要集中以下两个方面,一种观点认为,法庭是世俗的官僚机构,约瑟夫·K的被捕和受害体现了社会力量对个人的压迫。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法庭是神圣的,具有绝对的权力和公义,约瑟夫·K的罪过导致了他的被捕和死刑。应当说,这些观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助于理解《审判》,但却各自忽略了小说的一些关键因素,第一种观点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将法庭对应于某种现实的权力形态,因而对法庭隐而不见的神秘性和约瑟夫·K最后的自省没有给予充分的阐释;第二种观点从传统宗教角度,直接将法庭等同于上帝的神圣公义的力量,则忽略了小说所描写的与法庭有关的种种世俗征象,而小说并末指明的约瑟夫·K之罪在他们那里清晰起来,这种在上帝幌子下获得的自明性真理同样值得警惕。
巴别塔的权力主题渗透在卡夫卡的作品中,《审判》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巴别塔,但它所描写的世界图景却遵循着巴别塔的结构模式,即法庭及其所代表的法律为人为建构起来的权威偶像,成为支配世界运行和控制人物命运走向的本质力量。
人类建造巴别塔本意是要用一种客观的权威偶像来保护人的自由和生存秩序,然而;由于巴别塔是人自身权力欲望的投射,因此;它受制于人的欲望本身,具有任意建构的主观性。卡夫卡对巴别塔选择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指出了巴别塔结构的悖谬性,即建构巴别塔最终会走向自由的悖反,权力欲望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使人丧失生存的确定感。在《审判》中,法庭与法律为人为建构起来的权威偶像,由受制于人的主观权力欲望而无法成为客观的公正力量,因为,人们认同它并非纯粹出于对自由和公正的诉求,更是试图通过依附权威偶像来保障个人的合法存在和权力欲望的实现,这样,树立和巩固权威就成为根本目的,追求自由和秩序的初衷反而被降在其次。小说中所有试图“帮助”约瑟夫·K的人,不是将他引向自由,而是为了控制他教他顺从权威。卡夫卡将律师、画家、教士作为“帮助”约瑟夫·K的人出现是典型而富有深意的。
律师作为法庭与被告之间的中介,本应为被告辩护,以证明他的清白无享,助其恢复人身自由,从而彰显法的公平与正义。但霍尔德律师无意于践行这一职能,他从属于法庭的权力结构,用维护权力体系的论述打消被告显露出的改革司法制度的热情,并宣称:庞大的社会机构有其内在的运行法则和平衡力量,个人是极其渺小的,通过个人的努力想改善社会状况不但不会取得成效,反而会使个人的利益受损。所以,明智的做法是适应现存条件,安于自己的位置,通过斡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保自己的合法性生存。如果霍尔德斡旋关系是为了保障被告的合法生存,那也说明他履行了职责,即便其所使用的方式令人诟病。然而,霍尔德的真正目的却是为了控制被告,他除了从属于大的权力结构外,还在建构着小型的巴别塔,企图在自己的位置上实现对他者的控制。
画家是艺术的使者,肩负着发现和批判现实世界的缺陷,引领人超越日常生活的琐屑进入审美的自由境界的使命。从表面上看,画家蒂托里超然于世俗之外,居住在由人们施舍的楼顶的阁楼间,与一群孩子厮混在一起,保持着艺术家独有的清贫和童心,然而,蒂托里很少从事自己的艺术事业,其主要的工作是为法官画像,他以自己的才能为权威势力推波助澜,法官的权力在某种程度上即是由艺术符号建构起来的。现实中的法官大都猥琐、无能和骄横,画像中的他们却充满威仪,蒂托里有时还会在法官像背后画上司法女神,意指法官就是法的代理人、法的偶像。凭借为法官画像的“荣耀”,蒂托里在法院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在对待约瑟夫·K的事件上,他与律师的论调基本是一致的.即试图将K重新拉回到权力体系中,通过依靠权力、斡旋关系暂时获得安宁,由此,审判并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无名之罪也不能得到最终的赦免。
在人的职务等级中,教士与世俗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是人心灵的守护者,担负着引导人们进入信仰的自由境界的资任。然而,现实中教士却充当了建构巴别塔的最后一步,并使之“通天”的角色。约瑟夫·K期望教士能给他决定性的忠告,以使他能从案子中彻底脱身,过上自由生活。教士确实给了K中肯的建议,并给他讲了乡下人寻求法的寓言:下人来到法的门前,求见法,被守门人拦住,通向法的大门一直敞开着,他决定得到许可后再进去。在漫长等待的岁月里,乡下人曾反复地尝试,用烦人的请求、用丰厚的贿赂,希望能获准进去,但都没有成功。生命行将结束之际,乡下人模糊的双眼看见一束光线源源不断地从法的大门里射出来。教士向约瑟夫·K介绍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各种解释,试图把他从“理解”、“解释”引向“信仰”。但教士的信仰同样沾染上了世俗的内容,诉诸权威,他认为,守门人是法的仆人,隶属于法,“怀疑他的尊严就等于怀疑法本身……”不必承认他讲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只得当作必然的东西而予以接受。如果说画家是用艺术符号对权威进行神化,其虚构的方式还让人产生怀疑,教士则将权威直接提升为活生生的信仰对象,这样,“法”就从一般的秩序符号上升为一种神权代码,人们不但要信仰它,还要相信和遵从它的代理人。巴别塔经过教士这一环节,真正变成通天塔。教士的信仰在约瑟夫·K看来,是在“把谎言变成普遍准则”,因此,教士是无法为K提供精神坐标,给予他内心自由的。正像教士承认的那样,他也属于法院。
律师、画家、教士的存在表明常人所应拥有的两种最基本的自由,即人身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然而,在小说中,他们都走向了自由的反面,而且以对权力认同的共谋进一步威胁着约瑟夫·K的生存确定性。如果说人会由于主观的权力欲望僭越自己的职责,束缚他人的自由,那么客观的“法”则是实现人的自由的保障。然而,客观的、能够保障人的生存秩序的“法”是否真正存在,是作者提出的问题。
在《审判》中,判决约瑟夫·K的法也是一个秘密,被藏匿在无数道门之后,律师、画家、教士、法官以及许多普通人都充当着守门人的角色,法不再是施行公义的力量,而成为众人一致建构并守护的权力符码,这样,法的代理人、代理机构便成为掌控人们的命运之神。约瑟夫·K渴望弄清楚自己的处境,以便摆脱审判,重获自由,但外部环境却总是诱导或逼迫他顺从权威,自觉遵从权力法则。他最终也认识到:“从任何角度来看,法院都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机构,其全部工作一个刽子手就能胜任。”如果说强力意志是世界的通行法则的话,与强力意志相对的则是“虚己”,在基督教神学中,“虚己”是指上帝通过通成肉身,虚其神性,并以受难的方式警醒和拯救世人。基督“虚己”的拯救是人类理想的高标,常人难以企及,即便如此,“虚己”作为一种终极性价值则可在人的精神层面得以体现,比如自我贬抑、谦卑、祈祷、受难、忍耐、自我倾空等。
约瑟夫·K的死在另一重意义上加以理解,即他的拒绝反抗、安静受死昭示的是对“虚己”的模仿。在生命已被胁迫至死亡边缘的极限境遇里,约瑟夫·K“推波助澜”,以自我放弃的方式实现了自由的最高境界,即不是通过认同权威或扩张强力意志获得自由,而是通过抑制强力、自我倾空实践自由。之所以说是模仿虚已,因为约瑟夫·K的虚己并不具备神学层面的虚己所指的基督为世人开罪的救赎意义,而是卡夫卡对超越巴别塔的出路的探寻,它具有的是问询和启示的意义。
自我罪感
在卡夫卡看来,罪感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完全可以用“我罪故我在”来形容。在卡夫卡的笔下罪感的痛苦与自我的存在是紧密相连的。罪感是个体性的,只有当个人意识到自我的存在并开始探询自我存在的意义的时候,罪感才会油然而生。在存在论中,“自我是一种自身与自身发生关联的关系。”K的被捕就是K自身与自身发生联系的开始,也是K的“自我”的觉醒。K的被捕提醒了K的自我存在意识,他对生活的视角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开始更多的关注着自我本身,他由对“我”是否有罪的这个问题的思索开始了漫长的自审之路。当怀着满腔的热忱来关注自己是否真的有罪的时候也是K开始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
被捕使K由一个被自身的身份、地位等等世俗的禁令捆绑着的人,变成—个只关注单纯生活,关注自我的自由人:K的天性(欲望)使得他要尽可能的享受着现有的生活,同时也导致了他更深的陷入了罪的泥沼。这样,K的生活变成了这样—个循环,越追寻生活的真谛,他的恶感就越深刻,他就越关注生活本身。K只要活着一天,K的罪就会有增无减。尽管K没有完全的了解法律世界,然而在K每次进一步触犯法的时候,K的内心总有某种东西呼唤着他意识到法的存在,呼唤着他去直面这场审判,尽快的进入法的世界。K内心的这种向着法的力量就是K的罪感,这种罪感虽然常常被K主动的忽略,但是却无时无刻的不在起作用,这种罪感与K的天性(欲望)暗暗的进行着较量,每当K的天性(欲望)让K太过放纵生活时,他的罪感就会跳出来让K重视这场审判。就这样,在罪感的指引下,K一步步直面真实的自我,最终意识到审判的不可避免,意识到自身的罪是无法洗刷的,再多的反抗也只是徒劳,那只会加深他自身的罪,而无法改变定罪的事实。
《审判》是卡夫卡以K为例对人类的自由意志的一次探索过程,同时也是卡夫卡的一次深刻的自我审查,是他对自身的一次纵向的深入考察:对卡夫卡来说,自我是比全人类更重要的角色。卡夫卡终其一生去寻找的不过是如何使自己更好更健康的话下去,这是他对“自我”进行探寻之旅的出发点与终结点。
艺术特色
荒诞
所谓荒诞,也可称为怪诞,就是对事物极度夸张的一种方法。即从某种主观感受出发来改变客观事物的形态和属性,直入现象的至深之处,揭示事物的本质。因此,表现主义作家往往把形象、情节荒诞化。
小说中,作者描写负责看守约瑟夫·K的人;“那人生得身材细长,但很结实,穿着一套十分称身的黑衣服。衣服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口袋、袋子、纽子。还有一条腰带,好像一套游客的服装。因此,显得十分实用,虽然叫人弄不懂干么要穿这种衣服。”这样的看守形象不合常理,让人很难想象。而看守身上的服装无异于奇装异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会看到这样的穿着,但正是这种奇异和扭曲反映了作者内心深处的抑郁和恐惧。
主人公约瑟夫·K无辜被捕,稀里糊涂接受审判。他徒劳地做着挣扎,却在法律的罗网中越陷越深。他变得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紧绷的神经似乎随时都会断掉。这样的描写夸张生动,深刻揭示了主人公的主观感受,生活中充满了灾难,人随时会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荒诞的情节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的非理性,在非现实的事件和非现实的人物描写中折射异化的、充满痛苦的现实世界。这种表现主义的创作手法力求表现强烈的社会情绪和复杂的内心世界,成为“卡夫卡式”的创作风格。
象征
小说《审判》中的很多形象都有很深层次的象征意义。卡夫卡力图通过这些象征形象来表达自己对于社会、人和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解。小说中的法庭就具有神秘的象征意义。它并不是人们惯常理解的干净、明亮且肃穆的,而是被安排在了破旧的阁楼上。法庭在人们心中的形象既清楚又模糊。它不大,却具有无上权力,像盘旋在最高处的恶魔企图把一切人吞噬。法院的人并不正直,但不妨碍法律这部机器的照常运转和最后将它的捕获物置于死地。约瑟夫·K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既软弱却又并不甘于被诬陷。他害怕权力却也在同黑暗的司法制度作斗争。在法庭上的演讲,表现出他的坚强,但最后在被杀害时,他意识到反抗的毫无用处,而被顺从地带走。K象征着千千万万社会中的人。他具有性格上的双重性。而纵观他从30岁生日宣布被捕到被杀害的这段过程,纠结于权力、爱情,渴望着事业成功,却难于摆脱社会、命运捉弄,自我审判到被真正审判的过程也是象征着人的一生。
这种象征正是表现主义文学侧重表现抽象的情感,体验、异化以及境遇的具体体现。达到的效果就是小说在主题的表层结构模式多为寓言故事,不求表现社会生活,但求达到内涵深刻。